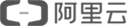作者:呂敬之 ?編輯:吾人 來源:融中財經 (ID:thecapital)
當“碳中和”被寫進各國法律,鋰電池曾是資本市場最硬的信仰:十年產能擴張五十倍,龍頭市值沖破萬億,融資額屢創紀錄。
然而,劇情急轉直下——價格雪崩、庫存高企、巨頭破產,歐洲一度最閃耀的雙子星Northvolt與BMZ在近日相繼申請保護,合計負債百億美元,千億級投資面臨減值。
需求減速、技術斷層、地緣切割三重壓力疊加,行業從“產能即正義”墜入“現金流為王”的殘酷淘汰賽。舊敘事破滅之際,新材料、新工藝、新循環、新供應鏈正在暗流涌動,它們指向一個更精細、更低碳、更區域耦合的TWh未來。
泡沫退去,真正的升級路徑開始顯現,全球鋰電池產業正站在洗牌與重生的十字路口。
鋰電池巨頭,申請破產
德國老牌電池企業BMZ正式申請破產保護。
歐洲本土電池產業再遭重擊。德國老牌電池制造商BMZ集團(Battery Manufacturing Zentrum)在近日向阿沙芬堡法院提交破產保護申請,理由為“流動性危機”。這家成立于1994年的企業,曾是歐洲領先的鋰電池系統供應商,客戶覆蓋工業、儲能、醫療及電動交通等多個領域。
BMZ在聲明中坦言,失去一家核心儲能客戶成為壓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該客戶訂單占其德國總部收入的30%以上,訂單驟停導致公司季度收入下滑40%,現金流瞬間斷裂。此前,股東曾緊急注入5000萬歐元紓困,但仍未能阻止危機惡化。破產申請文件顯示,公司賬戶一度僅剩720萬歐元,不足以支付員工薪資及供應商貨款。
此次破產申請涉及BMZ德國總部及其兩家子公司——BMZ Germany GmbH與BMZ Holding GmbH。由于子公司資不抵債,母公司因承擔連帶擔保責任被迫同步申請破產保護。不過,公司強調,其位于波蘭、美國、中國等地的海外子公司不受影響,將繼續正常運營并履行客戶訂單。
BMZ的困境并非一朝一夕。近年來,公司試圖從“電池組裝”向“電芯自研”轉型,曾收購TerraE品牌并計劃建設德國首座大型鋰電池工廠,但至今未能實現本土量產,仍依賴亞洲供應商。高額投入未能轉化為競爭力,反而加劇了資金壓力。
隨著破產程序啟動,BMZ已獲準啟動“自我管理”模式,由現有管理層制定重組方案,以期在法院監督下完成債務調整與業務重構。然而,市場對其前景普遍謹慎。分析人士指出,BMZ的倒下再次暴露歐洲電池產業在成本控制、技術迭代與供應鏈整合上的短板,追趕中國廠商的難度日益加大。
繼Northvolt之后,BMZ成為又一家陷入危機的歐洲電池標桿企業。歐洲“電池自主”之路,愈發艱難。
BMZ集團(Battery Manufacturing Zentrum)1994年由工程師Sven Bauer在德國巴伐利亞州卡爾施泰因創立,最初只做“來料加工”——從中國、韓國采購鋰離子電芯,在德國本土完成模組和系統集成,憑借低門檻快速切入電動自行車、園藝工具、醫療器械等利基市場,一度成為亞洲電池在歐洲的最大買家之一。
三十年間,公司把“組裝”做到極致:全球布局生產基地(中國深圳、波蘭、美國弗吉尼亞)和研發中心,員工峰值超3000人,生產面積逾19萬㎡,年交付項目100+,客戶名單涵蓋飛利浦、斯蒂爾、凱傲、戴姆勒客車、Solaris等一線品牌。2021年營收攀至4億歐元,并傳出IPO計劃,估值一度高達20億歐元;德國女首富、寶馬繼承人Susanne Klatten通過旗下SKion GmbH收購20%股份,為歐洲“戰略自主”站臺。
業務線上,BMZ從消費電子、工業工具一路做到商用車動力電池和大型儲能系統,曾簽下“歐洲史上最大客車電池訂單”,并與Eurabus、Kion成立合資項目,意圖擺脫對亞洲電芯的依賴。然而“自主造芯”投入巨大,本土超級工廠遲遲未能量產,疊加2024年能源價格暴漲、供應鏈紊亂,公司高度依賴的儲能大客戶突然砍單,占德國總部收入30%的訂單瞬間蒸發,現金流斷裂,最終于2025年10月27日向阿沙芬堡法院申請破產保護。
早在2021年,公司曾計劃通過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進行IPO,并設定了約2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60億元)的估值目標,但最終并未成功推進上市進程。
鋰電池的“災難之年”
這已經不是今年第一家鋰電池巨頭申請破產了。
今年年3月12日,Northvolt,這家曾被寄予厚望的歐洲最大鋰電池制造商向瑞典法院提交了破產申請,終結了其“歐洲寧德時代”的夢想。盡管公司在2024年11月曾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試圖通過重組自救,但融資努力最終未能成功,賬面現金僅剩3000萬美元,而債務卻高達80億美元,資金鏈徹底斷裂。
Northvolt的故事始于2015年,彼得·卡爾森與保羅·塞魯蒂兩位前特斯拉高管在瑞典創立這家公司,提出“歐洲電池自主”口號,目標是到2030年拿下歐洲四分之一市場份額,產能達到150GWh。憑借“去亞洲化”敘事,公司迅速聚攏資本,大眾、寶馬、高盛、貝萊德等巨頭累計投資超130億美元,簽下約550億美元長單,估值一度升至200億美元,上市計劃呼之欲出。2019年,首座工廠Northvolt Ett在瑞典謝萊夫特奧動工,設計年產能16GWh,隨后在德國、波蘭、加拿大同步規劃新廠,并成立回收子公司Revolt,試圖打造從礦山到回收的閉環。
然而,產能爬坡遠低于預期,Ett工廠2022年初才交付第一批電芯,良品率長期低于80%,到2023年底全球有效產能不足4GWh,僅為規劃的一成。管理層將問題歸咎于工藝復雜,但供應鏈人士指出,核心原因是缺乏成熟中試數據就倉促上量,設備與工藝參數匹配失敗。2024年6月,寶馬以多次延遲且質量未達標為由取消價值20億歐元的長期供貨合同,沃爾沃、大眾也相繼縮減訂單,公司收入預期從2024年的15億美元驟降至不足3億美元。為穩住現金流,Northvolt于2024年9月全球裁員20%,暫停德國和加拿大工地,并向美國法院申請Chapter 11破產保護,希望爭取10—12億美元新資金,但潛在投資人擔憂擴產支出無底洞,談判破裂。
2025年3月12日,Northvolt向瑞典法院遞交破產申請,賬面現金僅剩3000萬美元,而債務已攀升至80億美元,成為瑞典現代史上最大破產案。進入破產程序后,資產被分拆拍賣:美國鋰硫電池初創Lyten以約1億美元收購加州Cuberg航空電池工廠,隨后再以5億美元總價拿下瑞典Ett超級工廠、德國Northvolt Drei工地、波蘭Dwa儲能系統廠及全部知識產權,合計已建及在建產能逾30GWh;原總部研發大樓與實驗設備由瑞典國有電力公司Vattenfall接手,計劃改建為國家級電池測試平臺。Northvolt品牌名被注銷,歐洲唯一實現商業化量產的本土動力電池企業宣告消失。
復盤敗因,技術冒進是首要問題:跳過磷酸鐵鋰成熟路線,直接上馬高鎳三元加硅碳負極,導致良率長期低迷;市場層面,歐洲電動車增速2023年起明顯放緩,ACEA數據顯示當年歐洲純電銷量增長僅10%,遠低于2022年的20%,Northvolt仍以“產能即正義”的邏輯激進擴張,造成巨額折舊;管理層面,創始團隊多為供應鏈背景,對大規模化工制造經驗不足,生產、質量、設備三大部門各自為政,關鍵工藝參數無人拍板,問題層層積壓。Northvolt用十年時間演繹了一場典型的“歐洲工業浪漫”,在資本與政治雙重催熟下,技術與市場未能同步成熟,從200億美元估值到80億美元債務,既是一次昂貴的試錯,也為后來者留下寶貴的工藝數據、廠房設備和人才儲備。歐洲動力電池的故事翻過了充滿理想主義的一章,接下來將進入更加現實和精細的下半場。
鋰電池賽道的未來
鋰電池產業曾被視為碳中和時代最硬的賽道,短短十年間全球產能從幾十GWh躍升至近1.5TWh,然而盛宴背后,結構性過剩與路徑依賴同時襲來。
2024年起,動力與儲能電池價格暴跌四成,高鎳三元電芯跌破每瓦時0.5元,磷酸鐵鋰逼近0.3元,全行業毛利率被壓縮至個位數,中小企業在盈虧線上掙扎,即便是頭部廠商也靠規模效應和政府補貼維系薄利。
更棘手的是技術迭代窗口縮短,磷酸鐵鋰方興未艾,磷酸錳鐵鋰、半固態、鈉離子、無鈷高電壓正極便接踵而至,產線尚未折舊完畢就面臨被顛覆的風險,動輒數十億的資本開支成為沉沒成本,企業陷入“不投等死,投了找死”的囚徒困境。
地緣政治與貿易壁壘進一步撕裂統一市場,美國對中國電池征收高額關稅并限制含疆材料,歐盟強制碳足跡與本地化回收比例,印度、巴西提高進口關稅,全球供應鏈被迫重復建設,規模經濟被切割成區域碎片,運營成本陡增。
然而每一次過剩與震蕩都在為下一輪升級積蓄動能,困境恰恰勾勒出未來路徑。首要方向是材料體系迭代與工藝極限降本,磷酸錳鐵鋰將電壓平臺提升至4.1V,能量密度較鐵鋰增加15%,可與中鎳三元競爭,而成本僅提高5%,2025年開始在A級車主流車型放量;鈉離子電池憑借0.25元/Wh的BOM成本和-40℃容量保持率90%的優勢,在兩輪車、儲能柜、通信基站找到剛性需求,預計2026年形成30GWh級市場;高鎳三元走向9系超高鎳與富鋰錳基,正極可逆容量突破250mAh/g,配合硅碳負極能量密度可達350Wh/kg,為高端電動轎車和eVTOL提供續航方案;鹵化物固態電解質在室溫下離子電導率超過10mS/cm,與現有卷繞設備兼容,2027年有望率先在高端車型小批量應用,真正實現“半固態”的平穩過渡。
第二是制造范式從“減法”轉向“加法”,干法電極技術取消溶劑涂布,能耗降低30%,設備投資減少15%,特斯拉、寧德時代、松下競相導入,預計2026年成為主流工藝;3D打印電池把集流體、活性層、電解質逐層沉積,可將異形電池厚度控制在0.2毫米,為可穿戴、AR眼鏡、柔性電子打開設計空間;AI質檢與閉環控制把缺陷識別從“事后分選”變為“實時攔截”,輥壓張力、涂布面密度、激光焊接功率由算法毫秒級調整,良品率提升三個百分點即可攤薄成本0.02元/Wh,相當于一條10GWh產線年增利潤2億元。
資源循環從“合規成本”變為“利潤中心”,濕法回收工藝鋰、鎳、鈷回收率已超95%,磷酸鐵鋰正極通過再生補鋰可恢復容量至新料98%,成本較原生料降低20%,贛鋒、邦普、華友布局的“回收-再制造”一體化基地2025年起貢獻可觀利潤;歐洲強制8年電池護照與回收率目標,使車企愿意以高于市價10%的價格采購循環材料,綠色溢價與碳關稅減免共同構成商業閉環,預計2030年全球電池回收市場規模將突破400億美元。
供應鏈從“單點過剩”走向“區域耦合”,上游鋰礦在非洲、南美、北美多點開花,鹽湖提鋰、黏土提鋰、電解提鋰技術路線并行,把資源控制權從“三湖七礦”分散到“多極供應”,碳酸鋰價格有望穩定在8-12萬元/噸區間,既保障合理利潤又抑制投機;中游前驅體、正極、負極、隔膜、電解液在五大洲建設“近岸產能”,通過綠電比例、碳足跡追溯、本地化采購滿足各自市場準入,運輸半徑縮短使庫存周轉天數下降30%,資金占用成本隨之降低;下游整車與儲能品牌通過入股、包銷、共建產線等方式鎖定關鍵產能,形成“股權+長單”雙軌制,既避免重復建設又分享技術升級紅利。
當過剩產能被出清、技術路線分化完成、區域供應鏈重構結束,鋰電池行業將邁入“質量競爭”階段:能量密度、安全性、循環壽命、碳足跡、回收比例成為差異化指標,單純低價不再通吃,具備材料創新、工藝極限、循環能力和全球化運營的企業將在新秩序中占據高地,而跟隨式擴產、缺乏技術迭代的玩家終將被周期淘汰。未來的電池不再是標準化的大宗商品,而是融合材料科學、人工智能、綠色金融與區域政策的復雜系統,誰能在系統層面持續降本、減碳、提效,誰就能在下一輪產業浪潮中贏得先機,把鋰電池真正推向TWh時代的可持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