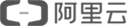來源:融中財經(ID:thecapital)?作者:王濤
漢堡王中國,換了一位“新老板”。
據界面新聞,2025年11月10日晚,CPE源峰宣布與漢堡王品牌達成戰略合作,雙方將成立合資企業“漢堡王中國”。
其中,CPE源峰將向漢堡王中國注入3.5億美元的初始資金,用于支持其餐廳門店擴張、市場營銷、菜單創新以及運營能力提升。漢堡王中國旗下全資關聯企業將簽署一份為期20年的主開發協議,該協議將授予其在中國獨家開發漢堡王品牌的權利。交易完成后,CPE源峰將持有漢堡王中國約83%的股權,持有漢堡王品牌的餐飲品牌國際集團(Restaurant Brands International,RBI)將保留約17%的股權。
在很多人印象中,快餐界能與麥當勞旗鼓相當的品牌一定是肯德基。但是放眼全球,麥當勞的真正一生之敵其實是漢堡王。雙方在美國經歷了數十年的商戰纏斗。在海的對面,漢堡王地位可以稱得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但如今的漢堡王站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一邊是進入中國二十年后終于迎來的控股權交接,一邊是自身多年積累下來的結構性難題——門店規模不上不下、品牌存在感有限、本土化節奏偏慢。新股東CPE源峰選擇在此時大舉押注,既是在接手一塊有些“老化”的國際資產,也是在下注一個仍有空間的長期賽道。
時間線如果拉長一點,會發現這并不是一樁孤立的并購新聞,而是一個更大故事里的關鍵一章節:外資快餐在華業務,正在經歷一場悄然的“股權本土化”。幾年前,麥當勞中國的大股東變成了中信系和凱雷;后來,肯德基、必勝客所在的百勝中國被拆分上市,引入春華資本、螞蟻等中國投資者;今年,星巴克中國宣布將多數股權出售給博裕資本;而現在,漢堡王中國的控股權又落到了CPE源峰手里。
外界看到的是一次次大額交易、一個個熟悉品牌背后股東名單的變化。真正值得關注的,卻是這背后商業模式的轉彎:跨國品牌更愿意做“輕”的那一端——品牌和體系的擁有者;門店、供應鏈和基層運營,則交給更懂本地市場的中國團隊和中國資本。
漢堡王中國被賣掉了
關于漢堡王中國這門生意“要被賣掉”的傳聞,并不是從官方公告那一刻才開始發酵。
如果把時間撥回到2024年底,漢堡王母公司餐飲品牌國際集團(Restaurant Brands International,簡稱RBI)的業績會上,管理層已經幾次點名中國區表現,用的關鍵詞很直接:業務一直在掙扎,和主特許經營商之間的矛盾在加深,相關協議已經進入終止和爭議處理程序。對于一家全球連鎖快餐品牌來說,這樣的公開表態本身,就是一種“預告”:這塊業務的現狀,總得有個了結。
被點名的對象,是與漢堡王中國合作十余年的土耳其TFI集團。自2012年拿下漢堡王在中國內地的主特許經營權之后,TFI一直是這門生意在中國的實際操盤者——選址、招商、加盟、供應鏈都掌握在這家土耳其公司手里。早期,它確實幫助漢堡王打開了規模:門店數從幾十家一路攀升到上千家。但疫情之后,門店盈利能力下滑、拓店未達預期、加盟質量參差不齊,多重壓力疊加,雙方的合作開始不斷冒出火花。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2025年2月。RBI宣布,以約1.58億美元從TFI及其他合作方手中收購漢堡王中國的全部股權,短暫把這塊業務“收歸集團所有”。在同一份聲明里,RBI還補了一句:接下來會尋找新的本地合作伙伴,重組在華業務。
這一步很關鍵。對外看,是跨國總部出手“接管問題資產”;對內看,更像是為下一步出售控股權掃清障礙——先把股權從舊合伙人手里接回來,再整體打包給新的買家,比在多方股東結構下直接轉讓,要簡單得多。
從那以后,漢堡王中國被放到了本土資本的視線正中央。行業里流傳的說法是:不少機構都和RBI有過接觸,詢問這塊資產的價格和條件。到了三季度,媒體已經開始報道,有幾家中國私募機構進入“最后一輪競逐”,其中就包括CPE源峰和紅杉中國。
真正敲定新東家的,是11月的一紙公告。
RBI對外宣布,與CPE源峰達成戰略合作,雙方將成立一家名為“漢堡王中國”的合資公司。按照協議安排,CPE源峰將向合資公司注入3.5億美元初始資金,持股約83%;RBI保留約17%股權,并與合資公司簽署一份為期20年的主開發協議——品牌和體系仍歸RBI所有,但在中國內地的開發權和日常運營權,交給這家以CPE為控股股東的新公司。
這意味著,進入中國整整二十年后,漢堡王中國的主導權第一次從跨國公司陣營,正式轉移到了本土資本手里。
新控股股東CPE源峰的背景,也讓這筆交易多了幾分想象空間。
這家機構的前身,是中信產業投資基金。經歷市場化拆分后,CPE源峰已經成長為一家管理規模在百億美元量級的本土私募股權機構,在科技與工業、消費與健康、基礎設施等幾個方向深耕多年。更被市場熟知的,是它在連鎖消費賽道上積累的項目:蜜雪冰城、泡泡瑪特、老鋪黃金、愛爾眼科、美麗田園、雍禾植發、絲域養發等等,都曾出現在它的投資名單里。
簡單說,它是那種“擅長做門店生意”的資本。
從雙方披露的信息來看,CPE源峰這一次扮演的,也不只是單純的財務投資者。一方面,3.5億美元的資金,將主要投向門店擴張、品牌煥新、供應鏈升級和數字化體系建設;另一方面,CPE也會把自己在連鎖項目上的那套打法——密集開店、單店模型打磨、激勵機制調整、精細化運營——系統地嵌入漢堡王中國的日常運營里。
對RBI來說,這樁交易給出的答案也很清晰:與其遙控一塊自己“啃不動”的市場,不如把控制權交給中國資本和本地團隊,自己退回到品牌方、系統方的位置,通過授權費、供應鏈服務費來分享未來收益。
對漢堡王中國而言,這一年則像是一次重啟——先結束一段“合作走到盡頭”的舊故事,再用一位新股東,開啟下一輪嘗試。
晚到中國的漢堡王,卡在了哪些“難題”上
在很多普通消費者的記憶里,漢堡王的形象有點微妙:它既是“全球三大漢堡品牌”之一,又似乎一直沒能在中國真正“出圈”。
漢堡王進入中國內地的時間并不算早。2005年夏天,它在上海靜安寺附近開出首店,當時的定位是“第三個洋快餐巨頭”,主打“火烤純牛肉”的皇堡,用足了品牌多年在海外市場積累下來的那套漢堡敘事。那家店兩層、上百個座位,媒體報道里不乏“姍姍來遲”“重磅登陸”這樣的表述。
但在消費者端,肯德基和麥當勞已經提前跑了十幾年。肯德基1987年進入北京,麥當勞1990年落地深圳,這兩家品牌早就通過瘋狂開店把網織到了全國各大城市。對不少中國人來說,“吃快餐”基本等于“去肯德基或麥當勞”。在這樣的市場環境里,漢堡王的“晚到”,注定要面臨先天的心智差距。
更現實的問題在于,漢堡王中國早期的擴張節奏并不算快。進入中國后的幾年里,它始終維持的是一個偏謹慎的步伐:門店集中在一線城市的核心商圈,開一家算一家,更多像是在“象征性”存在,而不是在主動搶占市場。從數字上看,前七年門店數量只有幾十家,在全國范圍內幾乎談不上規模效應。
直到2012年,故事才出現拐點。那一年,土耳其TFI集團獲得漢堡王在中國內地的主特許經營和開發權。新伙伴接手后,明顯把這門生意當成了典型的連鎖項目來推:加快開店節奏,引入加盟模式,往二三線城市下沉,試圖用規模來換品牌曝光和市場占有率。
在隨后的幾年里,這種策略確實帶來了門店數量的躍升:漢堡王中國很快突破了千店規模,開始出現在更多城市的購物中心和街邊商鋪里。對很多三四線城市的年輕人來說,第一次在本地商場看到“Burger King”招牌,就是那段時間的事。
然而,鋪開門店只解決了“看得見”的問題,并沒有自動解決更深層的挑戰。
首先是規模的尷尬。相比動輒上萬家的肯德基、幾千家的麥當勞,漢堡王中國的門店數量始終停留在一個不上不下的區間:多到需要龐大的供應鏈和運營成本來支撐,卻又不夠多,難以在全國范圍內攤薄這些投入。同時,門店密度不夠,也讓它在很多城市很難形成那種“走兩條街就能看到一家”的強存在感。
其次是品牌位置模糊。漢堡王一直強調自己是“懂漢堡的那一家”,用火烤牛肉、皇堡單品來區隔其他對手。但在中國消費者的日常選擇里,快餐更多是一種場景決策:中午匆匆吃個飯、加班隨便對付一頓、周末帶孩子去商場,小朋友要的是玩具,成年人要的是方便。肯德基通過早餐、本地小吃、夜宵承擔了大量高頻場景,麥當勞通過兒童套餐、咖啡、甜品把一家老小都抓住了,漢堡王則一直停留在“偶爾想吃個漢堡”的那個瞬間,缺少真正屬于自己的高頻入口。
再往后,是本土化的遲緩。肯德基在中國最出圈的一些產品——老北京雞肉卷、油條豆漿、辣翅、蛋撻——幾乎都是在本地團隊長期試錯下摸索出來的。相較之下,漢堡王的菜單長期以全球標準款為主,本地化嘗試的節奏明顯慢了一拍。早餐體系不突出,下午茶和夜宵場景挖掘有限,下沉市場小客單價需求又沒有被充分滿足,這在疫情后消費降級、價格敏感度大幅提升的環境里,消耗得更為明顯。
站在今天回看,就會發現漢堡王中國像是被卡在了幾道縫隙之間:規模不夠大,難以換來絕對勢能;品牌不夠鋒利,很難在年輕人心里留下深刻標簽;內部機制時常搖擺,在不同股東和合作模式之間轉換,缺少一套長期一致、適應本地市場的打法。也正因為如此,當CPE源峰選擇接手這塊資產時,行業的關注點并不只是“誰買了”,而是能不能憑借一套更接地氣的連鎖運營經驗,把這些老問題一一拆解。
國際快餐在華股權本土化,正走向“常態化”
如果把近十年來幾家頭部外資快餐品牌在中國的重大資本運作放在同一張圖上,會很容易看到一條清晰的軌跡:從簡單的“跨國公司獨資開店”,走向“品牌+體系仍在總部,門店和經營交給本土資本”。
麥當勞中國是這條軌跡上較早的一環。2017年,麥當勞決定將中國內地和香港業務打包,賣給中信股份、中信資本和凱雷組成的聯合體。交易完成后,中信系和凱雷合計拿走了80%的股權,麥當勞保留20%,并將大中華區未來20年的主特許經營權授予新公司。從那時起,麥當勞中國更多是一個由本土資本控股、以特許經營模式運作的區域公司,麥當勞總部則轉為品牌管理和系統支持的角色。
肯德基和必勝客所在的百勝中國,選擇的是另一條路徑:從百勝集團拆分出來,獨立上市,再引入春華資本、螞蟻等本土機構作為重要股東。資本市場的意義在于,讓這家原本由美國總部統一控制的中國業務,有了清晰的治理結構和本土化決策空間;從股權角度看,中國資本借由機構投資人的身份,深度參與了這家快餐巨頭未來增長的分配。
到了今年,星巴克和漢堡王相繼落子,則讓這條趨勢有了更具代表性的樣本。
星巴克選擇成立一家公司承接在華零售業務,再將這家公司的多數股權出售給博裕資本,自己退居第二大股東。漢堡王則通過CPE源峰引入新的控股股東,保留少數股權和品牌授權。從模式上看,兩者都延續了麥當勞中國當年的那套合資邏輯:本土機構掌握對門店網絡、資本開支、組織結構的決定權,跨國總部則通過品牌和體系綁定,穩穩享受一部分利潤分成,卻不再承受全部經營波動。
這背后,是跨國公司思路的變化。全球視角下,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依然不言而喻,但地緣環境更復雜、消費周期更短、競爭格局更激烈。繼續重資產擴張,意味著要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環境里承擔更多波動;相反,選擇把中國門店打包賣給本土資本,再通過長期授權費鎖定一條穩定的高毛利收入線,在財務報表上看起來更輕盈、更可預期,也更容易向全球股東解釋。
從中國資本的角度,這些外資快餐資產則具備了極強的吸引力:品牌成熟、現金流穩定、門店網絡已經鋪開,只要在單店模型、組織效率、下沉策略上做文章,就有機會在接下來的五到十年里持續釋放利潤改善空間。對管理著大體量資金的機構來說,這類項目既是兼具品牌故事與穩健回報的“壓艙石”,也為后續資本運作——比如再融資、上市、股權轉讓——留下了足夠多的選項。
更重要的是,本土機構并不是只把這些品牌當成“金融資產”,而是把它們看成一整套可以被重塑的商業系統。
以CPE源峰為例,它在連鎖消費領域的諸多布局,讓團隊對中國不同城市、不同客群的消費習慣有了更細致的理解:哪些城市適合鋪開大店,哪些區域更適合外賣小店;早餐、下午茶、夜宵分別有什么潛力;年輕人對價格、口味、社交屬性的敏感點在哪……這些洞察一旦被系統性地嵌入到一個國際品牌的中國版本中,就有可能改變這門生意原本的增長曲線。
從這個視角再看漢堡王中國被賣給CPE,就會發現它并非一樁簡單的“外企撤退”故事。更貼切的描述是:在國際品牌與本土資本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分工方式——品牌、體系、技術和全球經驗仍然掌握在原有總部手里,本地市場的具體經營和增長邏輯,則交給更熟悉中國土壤的人去打理。
這條路徑大概率還會繼續延伸。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幾年里,餐飲、零售乃至更廣義的線下連鎖服務領域,類似的股權本土化故事還會不斷上演。對中國市場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熟悉的國際品牌,會以一種“更本地”的姿態留在這里;對本土資本來說,這則是一條把全球成熟品牌重新“拆開重做”的長期賽道。
回到漢堡王中國這個具體案例上,它被賣給CPE既是階段性的終點,也是一個新的起點。二十年過去,品牌錯過過窗口,也吃過紅利,如今站在這一輪股權更迭的關口,它要回答的問題已經不僅是“誰是老板”,而是:在本土資本的加持下,它能不能終于找到屬于自己的那條中國道路。